
□甘敏求
缘起
每次见到黄耀红先生,总被他睿智而温暖的笑容所打动。
他是个自带芬芳的人,乐于成人之美,总是用真诚感染每一位朋友。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话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这些年来,他的畅销书出了一本又一本。但他自称是“中人之姿”,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篇古文:彭端淑的《为学》,“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
与黄老师交往十多年来,深知他的起点也是我们很多人的起点。一个平凡人,通过“旦旦而学之”,究竟能达成怎样的成就?
开学前后,又与黄老师小聚了两次,向他请教这种“可复制的成功”。
一、为学:40岁前未入文学之门
甘敏求:首先,要祝贺你今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你这入会,让作协在我们心中的公信力增色了不少。
黄耀红:哈哈,千万别这么说。现在入会标准好像是只要公开出版了4本文学作品集就可以了,我正好是4本,就这么入会了。能加入协会也有点小成就感,可能有更好机会与协会同道中人交流。
能写出好作品的大有人在。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作家,更适合的角色是一名教师。这个岗位是我现在安身立命所在。所以还是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加入作协。
甘:能出书的作家很多,但像你这样出精品畅销书的不多。很多作家在年轻时候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你也是从小就爱好写作吗?
黄:在写作上,我充其量只是中人之姿,也没有太多的文学才华。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我记得,1986年的高考作文题是《树木· 森林 ·气候》。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立马傻了,我压根就不晓得如何联系实际来阐发此三种的关系。匆匆忙忙中,自拟了一个题目,你绝对想不到,叫《改革改革,人人有责》,就像刷在乡间田磡上的某条石灰标语。
你想想,我那年十八岁了,高中毕业了,所谓的“语感”或所谓的“自我”,都还不曾建立起来。我不曾挣脱套话、大话的模式,也习惯于在文章结尾处喊几句干巴巴的“口号”。这不是我个人的愚钝,而是教化思维下的必然。
显然,那时候我的“生命”根本就还不曾打开过,也完全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话语,那是一个“自我”还未曾确证的阶段。令人惋惜的是,我很多有天分的同学,他们一辈子几乎就止步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思维与话语从未走出僵硬的话语模式。忘掉教育的内容,教育才真正开始。
多年后,这个句子令我感慨万千。按我当年的估分,我的高考作文应当才刚刚及格,60分里得到36分左右。
甘:那真可能因为写作影响了高考发挥。那年你考上了益阳师专,没能去读大学,在今天看来这不算一个好成绩。
黄:那时在乡下,只有考上和没考上的区别,谁考了什么大学,似乎也不怎么关心。我自己也不太懂师专与师大有多大的区别。心里没有这个比较,所以很开心就去师专了。而且,鬼使神差地偏偏读的是中文系。
甘:你师专毕业能直接分配到长沙市一中,这比较罕见。你在《一路还乡》中有篇文章《挥不散的记忆》,讲了这个历程。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帮你叩开了一中的大门。这也说明了你“中人之姿”背后的努力。
黄:是的,我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在师专读书时就跟长沙市一中马清泽校长有过书信上的交往,他对我写的字、文章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后来还专门派了四位领导去益阳考察我的情况。
甘:你在一中当了9年的语文老师,这段职业生涯是如何坚持写作的?
黄:1990年,我分配到长沙市一中担任语文教师。除了教案之外,偶尔也会写一两篇文章。其时,文字“举轻若重”,精雕细琢,充满着年轻语文老师的那份八股“匠气”。我不满于自己,最羡慕那些在文字里谈笑风生抑或云淡风轻的牛人。
我当时的文学阅读也不多,只记得连续买过弘征先生主编的《青春诗历》。八九十年代那些湖南“诗人”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很多,就缘于那本册子。
以我的经验来看,写作首先必须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当年我在长沙一中,并没有C刊综合症,每学年写写班主任总结或教学论文就挺好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南教育研究》(湖南省教科院办的一本内刊)发表了我的一篇班主任总结,全校仅有我被选上,这很给我鼓舞。
不久,我的一篇小论文又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上。领导与同事,似乎对我刮目相看。到了工作的第五年,我的另一篇论文又获得了“圣陶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二等奖。当时,好像是叶圣陶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吧,记得这个大赛的颁奖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次年,我再次获得这个大赛的一等奖。同榜的还有李镇西、黄厚江等今日名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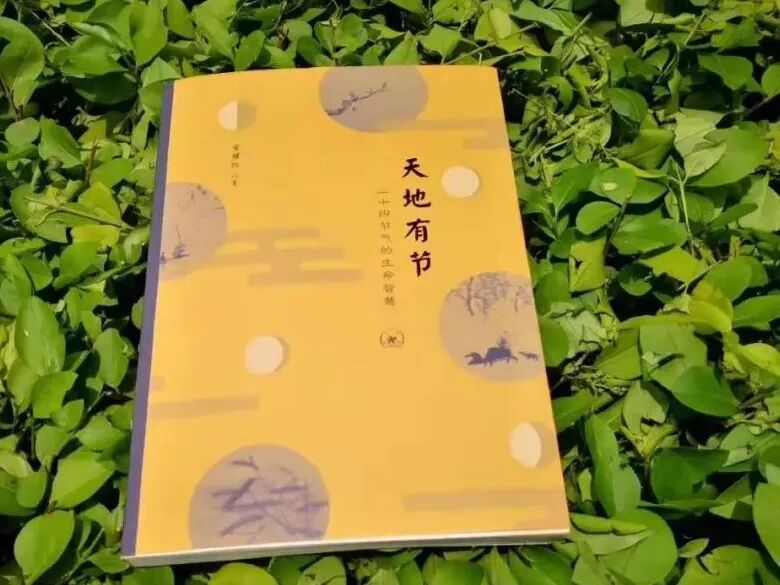
甘:1998年你跳槽到了《湖南教育》报刊社,天天要与文章打交道,与各界人物打交道,这应是个很大的转型。
黄:是的。最开始我的文字表达还是那种挺严重的“论文腔”,读起来紧巴巴的,板正有余,读来很累。特别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倾向,又造成文字的过分华彩。在写作上,我对自己的弱点,始终了然于胸。
编教育杂志,显然是一种文字生活。书写策划引语,加配编者按,撰写课例评论,报道典型人物或经验,一切都是编刊的刚需。就这样,我的写作路子稍微拓宽了一点。更重要的是,我的阅读世界也在慢慢打开。我的文字里,明显多了理论的“钙质”与文化的“厚度”。
写作一定要建立丰富的阅读基础。一个不读书的人,写作很可能只是重复的文字操练,那是不可能走得远的。很多年,我一直订阅《新华文摘》,期期必读,篇篇必读,这让我对不同学科的学术动态有一个比较前沿的把握。我那时最大的偏爱是李泽厚、韩少功,很多学者的文章我都兴致盎然。至今追随文字表达里的诗性与理性的交融,应当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术阅读。
甘:看得出你对学术的热爱。因为这段时间你还在湖南师大读了个教育学博士,而报刊社不像高校那样有学位要求。大家现在还习惯称你黄博士。读博对你写作有什么帮助?
黄:那时也是心血来潮,刚好四个好朋友一起聊天,冒出一起去读博的想法。2007-2008年,这一年我都在写博士论文。那是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那时候,整天都坐在电脑前。论文临近答辩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改到凌晨两三点。20多万字的一部书稿,当时真有那种泅渡沧海、横无际涯的苍茫感。论文后来被评为当年的“十佳论文”,那种磨炼,却是永生难忘。
2008年博士毕业,正好40岁,那时我还不曾写过任何称得上是文学的作品,除了博士论文叫“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之外,我几乎与文学没有多大的关系。
二、遇见:4本散文集背后的双向奔赴
甘:你说40岁前还没进文学的门,但之前的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早年的“论文腔”到后来的精致美文,你是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从《吾土吾湘》到《天地有节》,从《一路还乡》到《万年青翠》,聊聊这四本散文集背后的故事?
黄:我写的散文不多,一共才4本书,每一本都缘于某种遇见。
当时我主持《湖南教育》杂志,率先提出“湖湘语文”,倡导在地域文化下开发与建设语文课程。栏目就叫“湖湘语文行”,约了一些青年作家共同书写湖湘人物与胜迹,藉以构建湖湘语文的本土课程。
很多作家都被我约过了,一些人物和故居仍然没人写。有一天,朋友鼓励我:你的语言很好,是不是也写写散文?
就这样,我自己也试着写了一篇。我的第一篇散文就是发在这个栏目里的《汩罗江,从心头流过》。那时,沈念兄还在岳阳,我曾读到他一篇写洞庭湖水的文字,心下便佩服得紧。宗玉当时好像写了第一师范,他们的文字都是大开大合,充满着笃定与自信的气象。
写了“汩罗江”以后,我便萌生一个想法,不管别人写什么,我想写一个湖湘语文的系列。这样又慢慢去了贾谊故居,去了柳子庙,去了曾国藩的富厚堂,去了开慧与田汉故里,并且同步阅读了左宗棠、王船山、谭嗣同、宋教仁、齐白石等人的书籍。
那时真是精力旺盛,一个中午就可以写两千字。手头只要没有别的工作,我就沉浸在这些人物的世界里。
在朋友的帮助下,这些文字都曾在凤凰网国学频道登载过。到了2016年,《吾土吾湘》便由湖南教育出版社结为一集,柳理兄为之赐序。
这算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到这时,文字才似乎脱掉了一些论文腔。此书一印再印,后来获社科普及读物优秀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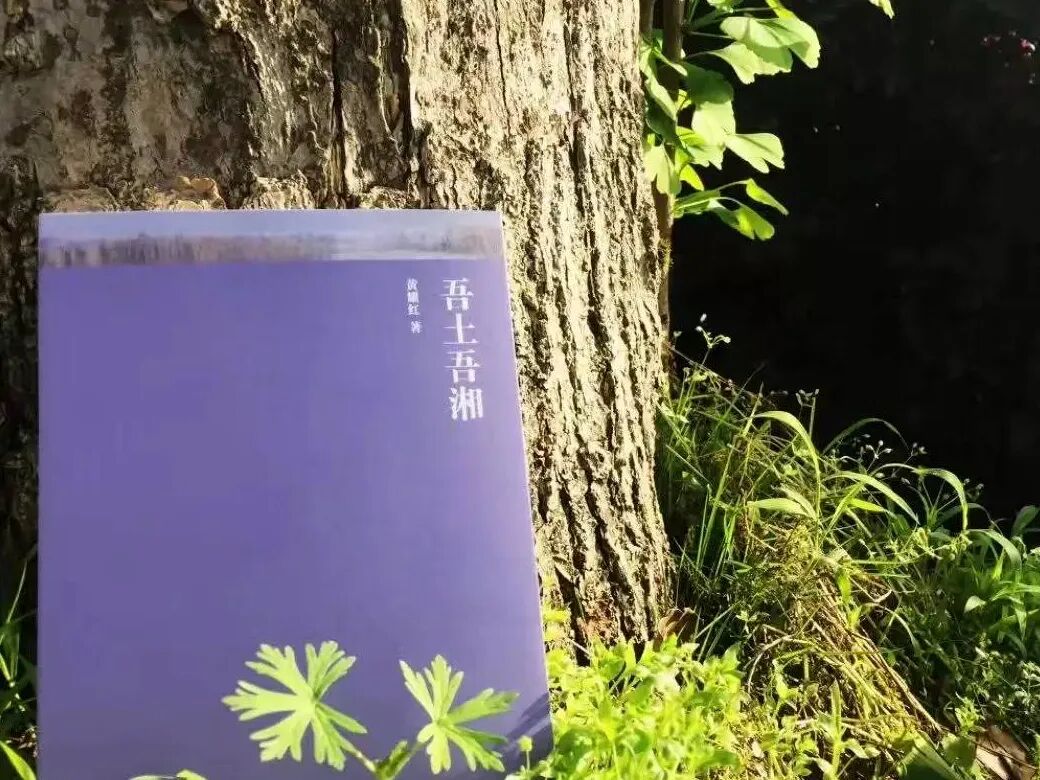
甘:《吾土吾湘》是一部很好的文化地理散文,没有《文化苦旅》那样的煽情。后来的《天地有节》似乎更能体现你精致美文的语言风格,更称得上你的代表作。这个转变背后又缘于怎样的遇见?
黄:《天地有节》最初的动笔,缘于我曾邀请著名绘本画家蔡皋先生去给湖湘教师读书论坛作演讲。就是那一次,我有幸结识这位“艺术家外婆”,特别是在她楼顶的紫藤花架下,先生以童年的率真话语跟我细数她的园子,细数她关于太阳、微风、花草、蜜蜂、鸟雀所带来的种种惊喜,那些话语和场景真是瞬间就唤醒了我青少年时期的土地与农耕的记忆。
我忽然就领受到耕读之于身心的意义,领受到此二字乃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力量。
耕,关乎天地自然;读,关乎思想文字。
生存与发展,形而下与形而上,传家与济世,其实都被这两个字道尽了。其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书已经不少。作为节气知识,AI工具更是瞬间呈现。但如果上升到智慧参悟的层面,这就不是AI可以取代的。
就这样,我用24篇文字迎候着24个节气的来临,我与四季开始了一个轮回的同行。最初的文章也发表在凤凰网。
又是因为朋友的成全,《天地有节》初版于三联书店,一印而再印,很多读者表现出特别的喜爱。主动朗诵书中文字的,从电视、广播及各种播主,不乏其人。五年后,漓江出版社再版《天地有节》,首印八千,再次受到读者的欢迎。
《天地有节》之后,文字的精致或许适合朗读。但是,我深知,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我在文字里的招式,比较单调,至今也找不到写小说的调子。这种缺陷,我很自知。
我曾在QQ空间里写过十多篇关于故乡的散文,很多朋友留言鼓励。疫情那几年,足不出户,我便将多年的散文整到一个目录里。朋友建议说,还是找一个“还乡”的主题比较好。
策划《天地有节》的朋友说,赶在春节前出一本《一路还乡》挺有感觉的。于是,又有了一本《一路还乡》。这里当然写了故乡的草木、风物、人情、往事,但我并不想它成为一片回不去的乡土。
甘:嗯,写完《一路还乡》,感觉你的写作风格越来越鲜明了。
黄:写作会带来人缘,也会带来“书缘”。或许是《天地有节》比较接近生态书写吧,当2023年岳麓山风景名胜管理局拟组织作家为岳麓山立传的时候,好几个圈内的朋友便极力推荐我作为《万年青翠》的作者。
岳麓山很熟悉,可是真正将山水、树木、鸟兽化为文字的时候,却又很不容易。打框架,写样篇,听讨论,我用40篇展开生态主题,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篇一篇写将下来。初稿出来后,又大改了三次。
此书作为岳麓山三部曲之一,与开林兄的《百年群英》,宗玉兄的《千年弦歌》放在一套书系里,自然又蹭到他们的“流量”,再加上此书由管理局出面组织,更是对接到更高端的资源。
我不敢说自己写得多好,只能说尽了力。这应当是我写作过程中非同一般的一次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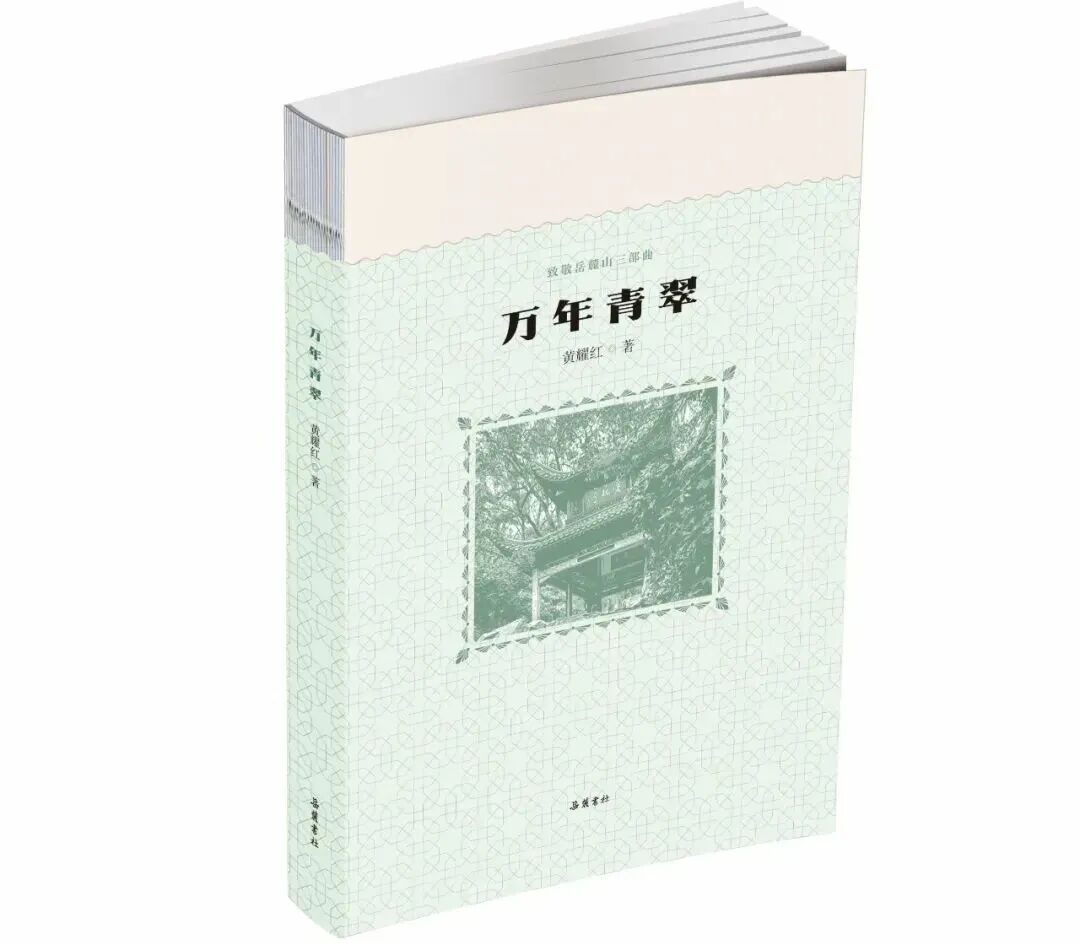
甘:写作与遇见,在你身上真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啊。
黄:对我而言,写作其实是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自我成长的方式。由中学教师到期刊编辑,再到现在的高校教师,文字的阅读和书写始终与自己的精神打开是同步的。
当写作真的成了自我成长方式的时候,一些奇妙的缘份就会奔赴而来。比如,你的朋友圈就会更多一些同道,一些同道又会在关键的节点上给你鼓舞,给你力量,给你成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其实并不孤独,它是一种温暖的传递。
我们说人文精神,人与文永远在一起。一旦写作,你就会更深地理解人,也将更深地结识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可能是“五十而知天命”吧,当下的我绝对没有这种“虚妄”的感觉。每次读到好的文字,自愧弗如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对同道的钦敬之情。
从写作主体来说,这种反思自我,不断看到自己不足的心态,不只是告别“文人相轻”的陋习,更重要的是让自我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悦纳他人和世界。
三、回眸:我自故乡来
甘:刚才你提到《一路还乡》的主题,近来我也多次听到一些学者、作家提到同样的主题。比如孟泽先生新书《君自故乡来》,他说“我们要从出发的地方寻找初衷、动机和可能性,需要从树根长出的地方重新寻找阳光和空间。”王立新先生在最近一次湖湘游学中也说,“思想家没有国界,但要有故乡。”没国界是因为不要自我设限,有故乡是要有自己的精神原点。在你心中,故乡是什么?
黄:我愿意将“还乡”当成一种现代人的精神之旅。因此,在《一路还乡》里,与血脉还乡并行的,是教育还乡与文化还乡。它是返回,更是重建。这本书出来之后,小时候生长在乡村的朋友或许更能共情。
怀乡、望乡是中国文学的母题,这个传统可以追溯至三千年前的《诗经》时代。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乡土社会。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读萧公权先生的《中国乡村》,读《田园诗与交响曲》,读鲁迅、沈从文、赵树理、路遥等人的乡土文学作品,我们对于乡土作为熟人社会的礼俗自治,对于乡土社会的组织方式,对于乡土的信仰、习俗、制度、建筑、服饰、饮食、民风的千百年绵延,特别是看到一百年多来的由“城乡分治”到“城乡一体”的伟大的近现代进程,我们总会对土地、对耕作怀着一种特别的深情。
这不只是古典的文人式的都市乡愁,还更多带有一种文化的寻根自觉,或是一种文明互鉴之下的启蒙自觉。
理解乡土中国,发展乡土中国,重塑乡土中国,振兴乡土中国。只要我们还相信“大地是母亲”,只有我们还相信“接地气”,我们的内心就一定连接着故乡。
这个故乡,当然并不止于老家、老屋、祖宗、家族之类,很多现代人其实是没有“故乡”作为栖居之地的。文化的故乡、精神的故乡、教育的故乡总是存在的。这些故乡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统、语言、文字里,存在于经典、文明和族类的记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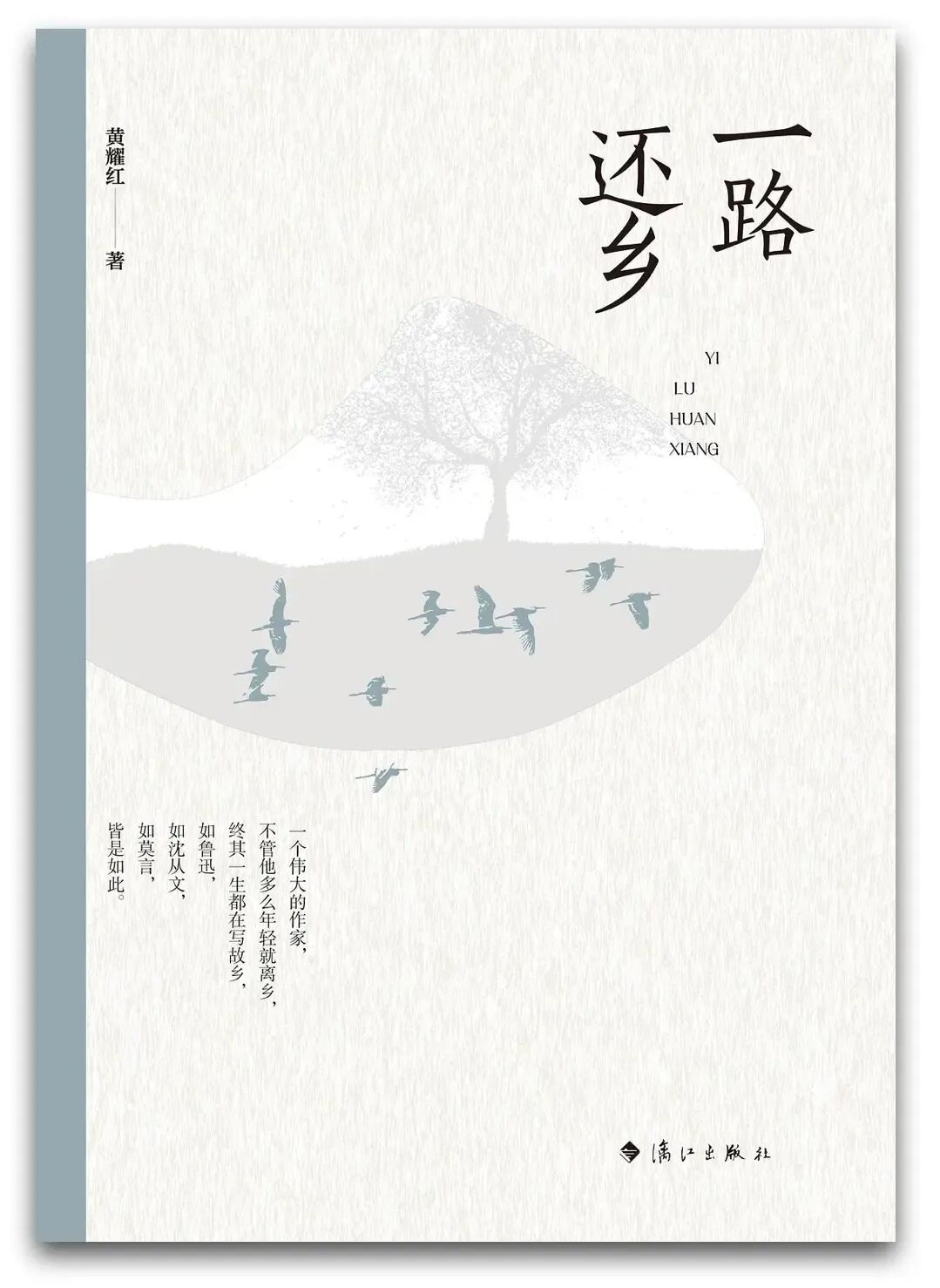
甘:现在的年轻一代还有乡可还吗?或者说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原乡?你笔下的那个故乡棠坡,还能带给你小孩故乡一样的感情吗?
黄:很难了。像我孩子这一代,他们除了春节或平常节假日回到他的祖籍地,对于棠坡、对于我所写的老屋、白果树以及各种草木和吃食,他显然不曾有过体验,他也不太可能与这些物事建立起情感的连接。
但是,他现在也是一名语文教师,他在课堂里也得讲《乡土中国》,也得讲士大夫在感喟“人生如寄”的同时,无数素朴的农人却始终相信“人生如植”,他从“种豆得豆”的种植里得到一种人生启示也就很好了。
甘: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棠坡已不是你小孩心中的故乡,但你的文章、你描述的那个棠坡,依旧可成为他精神的故乡?
黄:也许很多年以后,我小孩会觉得这块地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会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会告诉小孩,这里是他生命来龙去脉的一个起点。父母是我们的来处,那么父母的家乡当然是我们回望的一个去处,一个时空的原点。
他不一定在这里生长,但这里一定会成为一个精神象征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精神的原乡。
也许终有一天,他会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他会在汉语里打捞出“棠坡”这两个字,并从它的笔画间读到父亲的老家,他的祖籍,他能在回望中看到故园依稀的灯火。我想,那可能会是他面朝世界、春暖花开的幸福时刻吧。
四、守护:永葆生命的敏感
甘:你的文字个性鲜明,尤其是《天地有节》,包括日常发的朋友圈,都保持着对天地自然的细腻描绘。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事物,到了你的笔下,则充满了灵动与生机,充满了对生命的敏感。你是如何保持这种敏感的?
黄:你所说的“生命敏感”,远非世俗所贬抑的多愁善感,更不是封闭自守的心性敏感,它表现为个体生命对于世间万物的惊奇眼光、灵敏直觉和独特感受,它是身体、心灵与世界的“同频共振”。
生命敏感,非但不是初级层次的感觉,相反,它所抵达的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生命妙境,那是一种超拔于语言、思维而直达生命慧根的自由之境。就像打球需要“球感”、读写需要“语感”一样,世界没有哪种“敏感力”的养成可以离得开具身体验与生命实践。
个体生命敏感力的大小强弱,与先天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是后天的培育。这种对感性世界的审美把握力,关乎直觉、想象与灵感,而非建立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推演之上。
在我看来,所谓生命敏感,它更多来自生命场域的敞开、生命感官的开发、与生命情意的浸淫。
甘:对于在钢筋水泥丛林里长大的一代,如何向他们普及生命敏感教育?
黄:我所理解的“生命敏感教育”,就是一种感性教育,即强调与生命共情的审美教育。
鲍姆嘉通最初提出美学构想的时候,就是不满于人类将感性视为理性的初级与附庸。他试图以美学的名义赋予人类感性以独特的价值。此时的美学,亦即感性学。实践表明:感情与理性之根本歧异,在于感性唤起的并不是人的道德感与认知,而是人的同情与共鸣。这种没有物我之分、人我之别的生命理解与生命同情,正好道出了“人之为人”的高贵本质。你提到的生命敏感,令我想起自己的中小学阶段。
我所读过的小学、初中、高中,是最普通的乡村学校,它们隔城市很远,离县城也不近。多年后,当我们走过城市的立交桥,看见无数背着书包的“名校孩子”走出校门时那一脸的空洞与黯淡时,我无数次庆幸过:幸好我一直在乡村学校学习成长。
如果你此刻问我,你最深的高中记忆是什么?最先跃入脑海的,并不是老师、黑板与复习卷,而是学校门前那口倒映着青山影子的池塘水域,或是黄昏时停在水边草茎上的一些红蜻蜓,又或是风一样穿过金黄稻田的骑行背影,甚至就是曲曲折折煤屑路边一片碧绿的菜畦,也可能是破旧教学楼外那些那么干净而素雅的白玉兰……
当年以为无比重要的话语与声音都已随风飘逝。很多年之后,我在写作《天地有节》的无数个午后,那些故乡的风物全都纷至沓来。
那时候,我才深切地意识到: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早就与大自然建立起了深深的连接。
比起数学方程式、历史大事年表或氧化还原反应原理,它要牢固一万倍。我甚至认为,我的美学启蒙与其说来自某一本书或某一位老师,不如说来自老屋门前的一树桃花或芋头叶上滚动的露珠,甚至是从对面山头升起的月亮,甚至塘基上的萤火,每个黎明报晓的公鸡或是深夜熟悉的犬吠……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极力反对现代知识教育对于现代儿童天性的戕害,他不惜偏颇地主张儿童回归自然回归古典生活。他的经验自然主义未必正确,也未必行得通。但是,我们今天谈论生命敏感教育,不可能绕开大自然去高谈阔论。因为,“天地”是教育的空间和资源,“四季”则是教育的时间与节奏。
一旦学校之“时间与空间”无法对应到天地、四时之变,那么,你能相信他可能培养出生命的敏感力吗?很可能,它所带来的只能是生命的焦虑和片面。
五、寄语:以舒展破“内卷”
甘:接着你刚才聊的教育话题,现在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可以用一个“卷”字来描述各自的状态。你如何看待内卷导致的中小学生身上的生命活力的萎缩?
黄:现在大家都说很卷。卷这个词用得很妙。一个语词往往就是一种境遇的写照。今日学校教育最大的一个流行词就是“卷”。这个字,它从来就站在舒展、舒张、舒服的对立面。
一片树叶的“卷”,意味着环境的酷热难耐,或是病虫来袭。当校园里偶然传来青春凋零的痛心消息,当抑郁成为蔓延的青春征候,当人们的时间被折叠成试卷与评价的时候,我想,生命教育就不只是生命至上的价值倡导,也不只是身心健全的人格理想,它必须体现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全面打开。
什么时候,教育不是“卷起”,而是“舒展”,那么,诸如每个生命的绽放才会真的拥有一个好的生态。
甘:你是教育学博士,工作经历也都与教育有关,有一大批中小学校长粉丝,许多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也是请你策划。你对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有何建议?
黄:有人说过,教育学是一个关系学。我想,这里所说的“关系”,更多地强调教与学之间的伦理秩序,与世俗功利层面的“关系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如何理解“关系”呢?
其一,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因此不可能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分散个体,它必然是相附依存的社会性存在;
其二,它也存于人与文化之间,人类因为文化而成为天地间独有的符号生命,并建构起精神的时空。
其三,关系存在于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如果回到盘古开天地的神话那里,我们会惊奇地看到,先民最朴素的创世观其实就是我们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生生不息的文化观。因此,盘古的眼睛、四肢、血液、呼吸与大自然日月、山川、风露之间从来就未曾有过主与客的分离,它们是建立在生命转化之上的前世与今生。
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人在关系中确证生命的基本坐标就是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自然。个体经验的丰富、拓展与超越,每个人的生命遇见、命运脚本、人间故事似乎都逃不出这个最根本的“三维关系”。
甘:当前这种内卷的状态,就是这“三维关系”出了问题?
黄:是的,长期以来,学校教育未曾在这个“三维关系”中找到平衡,其突出表现就是,人与文化的关系之维高度紧张,课程以庄重的名义形塑着成长中的生命,同时它也凭借着知识的傲慢切断了生命的连接,遮蔽了世界的丰富,以至于人与人的关系不断被世俗和功利所绑架,甚至冰冷的分数已然异化为压抑学生个性、摧毁学生幸福的沉重标签。
更重要的是,人与天地、与自然、与众生的情感连接,必然遭到单向度的价值挤压,而越发显其“无用之用”的低微和脆弱。
今日之学校生活,时间就是作息,就是课程表。刺耳的铃声淹没了四时与风雨的节律,巨大的电子屏幕虚拟出高山大河,凝固而切割的空间化装成“铁打的营盘”,即使就近在窗外的花树缤纷也无法吸引那些埋在习题间近乎呆滞的目光。
这时候,自然变成了“诗里的田园”,江流化成了“历史的隐喻”,月亮只是照着“秦汉的雄关”。再加上以手机为重要表征的视频化的电子传播,更是将青少年的世界引向虚拟与刺激。充满着审美惊奇的自然万物渐渐消失在数字化的声光化电之外。
人与知识世界之间的单向度“紧张”,不仅造成人为“知”役的精神焦虑与紧张,而且它将编织出束缚天性的巨大樊篱。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渐渐疏远,发生在生命之间的审美共情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
在现代都市拥挤的车流里,在熙来攘往的匆忙中,我们似乎找不到慢下来的理由。于是,更多时候,孩子们只在诗句遥想“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却又无数次忽略了“余霞散成绮”的窗外;他们在黑板前推敲着“春风又绿江南岸”,却又无视地从“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校园长廊里走过……
具体的理念与操作,不是我等几句话说得清,或者说了就有用的。
但至少,我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愿意道出一点常识:让教育更多地去亲近自然、亲近大地吧。只有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更好地亲近儿童、亲近未来。
来源:红网
作者:甘敏求
编辑:姜媚
本文为理论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theory.rednet.cn/content/646943/62/15318041.html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